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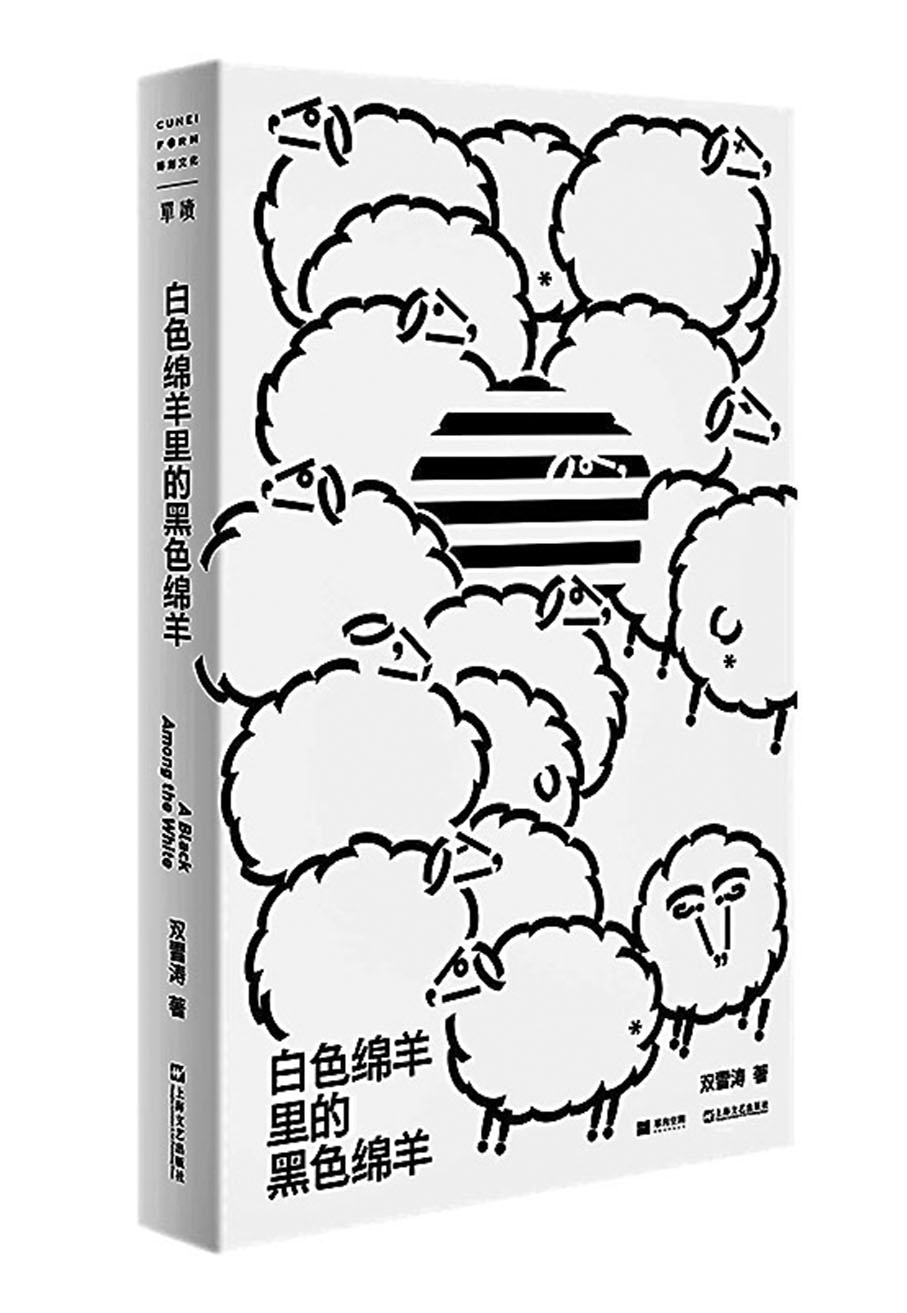
圍繞雙雪濤新作《白色綿羊裏的黑色綿羊》,日前華東師範大學教授毛尖、脫口秀演員鳥鳥、非職業寫作者賈行家,以及作家本人,共聚上海朵雲書院戲劇店,一同探討「在今天,我們應該如何講故事」。雙雪濤坦言,眼下對作家等故事創作者而言,課題的確變得很嚴峻,若寫不出精彩的故事,實難與短視頻等強大競爭對手抗衡。而生於上世紀七十年代的毛尖,則從滅蠅運動,旁批《茶花女》說開去,不由感嘆她童年時代聽聞的故事濃油赤醬,活色生香,相形之下今日多數故事稍顯平淡固化。◆文:香港文匯報記者章蘿蘭上海報道
青年作家雙雪濤1983年出生於遼寧瀋陽,2011年以小說處女作《翅鬼》獲首屆華文世界電影小說獎首獎。其最富盛名的作品是2016年出版的小說集《平原上的摩西》,次年同名小說獲第十七屆百花文學獎中篇小說獎。2018年,憑藉小說《北方化為烏有》獲首屆汪曾祺華語小說獎短篇小說獎。2020年,作品《獵人》獲第三屆寶珀理想國文學獎。《平原上的摩西》後被改編成電視劇和電影。
小說像氣球
由單讀和上海文藝出版社推出的《白色綿羊裏的黑色綿羊》,是雙雪濤出版的首部雜文集。全書主要收錄了作者面向寫作愛好者的專文、對電影和文學兩種藝術媒介的理解,以及自2012年辭職開始自由寫作後,十年來發表的其他與創作相關的雜文、隨筆、訪談。
書名《白色綿羊裏的黑色綿羊》來源於其中一篇雜文《人物非人亦非物》,主要是談如何建立小說人物形象。雙雪濤在文中回憶,初中時瀋陽曾發生連環出租車搶劫殺人案,此案轟動一時,令少年時期的作者深受震撼。後來,他想在《平原上的摩西》中使用這個素材,就計劃從因調查搶劫殺人案殉職的警察蔣不凡寫起。但在意識到並不是要寫一部偵探小說後,最終刪掉了這個部分,改由普通人莊德增起頭。「小說像氣球,你要保證它的壓力,不能老用針去扎它,」雙雪濤寫道,案子雖奪人眼球,也只是小說中事件之一,「它就像白色綿羊裏的黑色綿羊,但是要一起養。」
寫作的「無私」與「自私」
作為小說家的雙雪濤,在上海與讀者分享了與「故事」相遇的過程。他談到,自小受到的教育是要為集體服務,小時候總覺得寫小說是非常「自私」的選擇,因為這只是為自己幹點什麼事,似乎對別人無益,但這種玩法對「貧民」非常「環保」,只需耗上時間,不用花真金白銀,待寫出完整的故事後,自己也感到很快樂。
直至後來漸漸有了讀者,寫作不再只是一件悅己的玩具。「我和故事之間的關係要有『第三者』,就是看我寫故事的人,」他反覆強調讀者對他的重要性,「寫作需要讀者,否則就喪失了幾乎全部的意義」。基於此,他常常逼着自己首先要把故事寫完,因為寫完才會有讀者,而「沒有完成的小說,是不配去見讀者的」。
但對童年時的毛尖而言,寫故事非但不「自私」,甚至是「無私」的舉動。那是一個讀物匱乏的時代,手抄本非常流行。傳來傳去的過程中,常常遺失開頭結尾。毛尖回憶,她人生中的第一次「約稿」,就是給《一雙繡花鞋》續上結尾。
「有個手抄本叫《一雙繡花鞋》,表弟拿給我時,就沒有結尾,看完後我們非常痛苦。這時有人就說,『你作文寫得好,你來寫個結尾』。」毛尖真的完成了「約稿」,很快給《一雙繡花鞋》收了尾。之後不但在同學間爭相傳閱,甚至還被「催更」,「所以寫故事是具有公共性、很無私的舉動,是為了『造福』整個班級。」
那個年代還流行旁批,很多到手的書都有旁批,毛尖印象最深的是寧波圖書館的一本《茶花女》,就被註了很多旁批。「寧波圖書館有奉化、象山、寧海各地來的人,於是就看到有旁批寫『這個茶花女沒啥了不起』,然後開始講寧海茶花女的故事。再下個批註又寫『你們那個茶花女沒什麼了不起,我們那裏有個更厲害』。一段段旁批就是接龍各地『茶花女』的故事。雖然不太文明,但大家都很樂意讀這樣的旁批。」
故事匱乏的今昔
「在我的童年時代,我們自己就好像生活在故事中,做一些當時覺得普通,現在看起來匪夷所思的事情。比如滅蠅運動,大家把打死的蒼蠅帶到學校,每個同學都在課桌上分蒼蠅,把一個蒼蠅撕成兩個,就可以增加計數。學校公共衞生檢查時忘記帶自己的,就去掏鳥糞冒充,順便分給其他忘帶的同學。每個人都有故事,一個班級就有很多故事,故事對我們來說就是日常生活。」
「我們沒有手機、沒有互聯網,大家都是以『肉身』與別人碰撞,所以講故事的那些人,一定要把故事講得濃油赤醬,至少要比生活驚心動魄,」毛尖說,「不像今天,大家都宅在家裏,故事已經很稀有了,好像就只能在小說中讀到,一個自殺就能成為一個故事,看到高啟強(電視劇、小說《狂飆》中的人物)更成了一個事件。」
今昔對比,大家講故事的能力似乎有所退化。毛尖又說到,小時候有一次正上着課,教室裏突然闖進來一個男人,拉走了語文老師,瞬間班級裏人人都變成小說家,開始就此杜撰形形色色的故事。而前不久,她在一節創意寫作課上,讓學生根據上海最近發生的醫生殺妻案,站在那個醫生的視角,構思當時場景,學生們雖然都用了很好的修辭,但大多將醫生想像成鳳凰男,妻子則是上海本地的漂亮女孩,角度很是固化。
而在雙雪濤看來,從科學角度來說,今天講故事的難度確實增加了。他說,對故事創作者而言,課題變得很嚴峻,因為閱讀主要是人腦中的海馬體在作用,而瀏覽短視頻則會因刺激、打斷這種機制,在大腦另一區域產生快感,所以故事創作者要和這些能引起生理刺激的東西,去競爭一個能讓人停下來的「席位」 ,競爭非常激烈,而作家別無選擇,只能盡量把故事寫得精彩一些、有意思一些,如果讀者從中連閱讀的樂趣都得不到,競爭更無從談起。
當然,他在故事中追求的不僅僅是「精彩」和「樂趣」。「現在故事好像越來越貼近自我,不像以前巴爾扎克、托爾斯泰這種作家,手伸很長能掌握世界。不要說掌握世界,我們可能連掌握自己都費勁,能把自己寫好,表達自己想表達的東西,已經很了不起。但作為一個作家,無論是不是夠得着,還是不能放棄把手伸長的慾望。」






0 / 255