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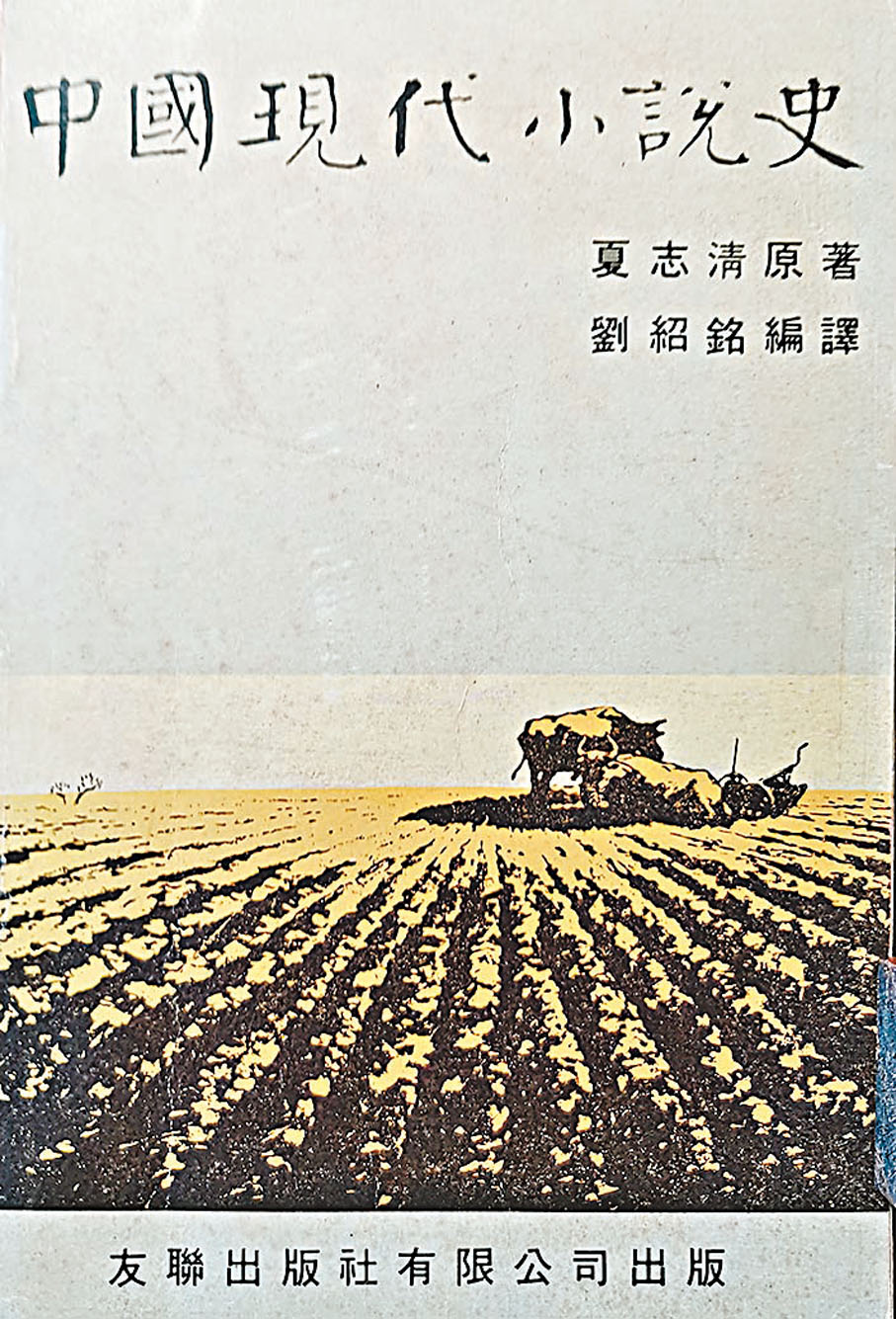

讀到劉紹銘教授1月4日仙逝的消息後,把悼念之情轉為重讀其書之事。劉教授1978年為夏志清教授《中國現代小說史》中譯本寫的序云:「校對時予我最大幫忙的是黃維樑。跟余國藩一樣,維樑是我近年先通信,後結交的一位年青朋友。」其實通訊之前,我見過劉先生。那時他是新科博士,來了香港,和九龍的「愛華居」一群文化壯年和青年會面。胡菊人、陸離等都在場,我還沒有從中大畢業,自然是叨陪末席,聽諸公意氣風發大談胡金銓電影《龍門客棧》獲獎的喜事。那應該是1968年。1968、1978……,然後是2018年在嶺南大學與劉先生的最後一次會晤了。◆文:黃維樑
幾個年份都有個8字。還有一個:1981年秋天,劉教授邀我到陌地生(Madison)威斯康辛大學的東亞系當客座副教授。寫信時他稱我維樑,或只寫W.L.。 到了威大,要我稱他Joseph,自此稱呼時西風壓倒東風。我教兩門課,一是高年級的文言文,一是英譯中國現代短篇小說選讀。後者用的是新鮮出爐的Modern Chinese Stories and Novellas:1919-1941,書由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出版,是夏志清、劉紹銘、李歐梵三人合作的結晶。1983年友聯出版社推出此書的中文版,Joseph(下面簡稱Joe)在《序》中記述我的「功勞」:我審稿又校對,且「把英文選集所附的作者簡介翻譯了出來」。
夏志清(1920-2013)的兄長夏濟安(1916-1965)是劉紹銘台大讀書時的老師,劉是夏志清的私淑弟子。夏公從1969年起,一直對我愛護鼓勵有加,我差點兒到哥大成為夏公的學生。有這樣的淵源,我為夏公、為Joe出點力,既樂意,也義不容辭。
「快樂時光」 快人快語
Joe的同事、《五四運動史》作者周策縱教授,把Madison翻譯為「陌地生」,又把居所稱為「棄園」,那種「太息啊不樂」(我對diaspora的「雅譯」)的感傷情懷躍然。不過,1981年秋的陌地生,有時也有沙龍式的小聚會:李歐梵和杜邁可(Michael Duke)先後在這大學客座或掛單,Joe的高足王德威正在此攻讀博士學位,當然還有東亞系系主任倪豪士(William Nienhauser)和其他教授。
東亞系在美國任何大學都屬於小系,那個年代各種文化學術交流不頻繁;清靜的校園,研究室「躲進小樓成一統」,正好潛心做學問。我認識的不少學術界朋友,都堪稱工作狂,Joe是個「勞模」。他每周教學雖只有幾個小時,但一周五六天以至六七天,天天朝八晚五或晚六,都把自己關在研究室裏,埋首於漢穆雷特王子所說的「文字,文字,文字」。大概每周一次,最多兩次,到五點鐘了,他來敲我研究室的門,說:「維樑,我們Happy Hours去!」
在酒吧裏,「快樂時光」一般是五點至七點兩個小時,所有飲品半價。我們常去的那一家,煮熟去殼的冰鎮大蝦,每隻賣二十五美分,我們飲酒啖蝦,誠然快樂。然而,二人談話,免不了感時憂國,那時白樺的電影文學劇本《苦戀》挨批。Joe喜歡的馬丁尼酒,以琴酒和苦艾酒攪拌調製而成。苦艾,《苦戀》,「快樂時光」,杯酒言歡也言悲,談文談出了百般滋味。
「感時憂國」,是了,夏志清教授有單篇論文題為「Obsession With China: The Moral Burden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」,作為其《中國現代小說史》的一個附錄。夏公這本名著的出版,Joe的功勞「罄竹難書」(注意我用了引號)。
「快樂時光」的過客,有時真是快人快語。Joe嚴肅為學,豪氣月旦。讚嘆人時點頭嘖嘖,有時露出俯首低眉之姿;斥罵人時一派粗線條漢子作風,廣東俚語迭出。做事總難盡滿人意,好友有時所為不美不善,Joe怒斥曰:「呢個人翻轉豬肚都係屎!」後來在香港客座,勤奮為學著述豐厚的劉教授,看到一些學系主任或學院院長不事學術生產,不屑諷曰:「霸住屎坑唔痾屎!」罵人用粗漢語言,論文化大事、家國大事,他則以硬漢姿態發聲。
其人其文 常顯率真
Joe是粵人,小時候是正牌的「香港仔」,粵語夠地道。他寫《吃馬鈴薯的日子》《二殘遊記》和《九七香港浪遊記》,就用了不少粵語詞句,我這個粵人讀起來當然覺得「過癮」。《吃馬》講留美工讀生活,男兒當自強,滿有鬥志。書在港、台多次重印,最為有名。Joe留美時做過唐餐館的「企枱」,我亦然,讀起來更感慼慼。《二殘》是小說,而寫實性強,妙趣橫生;在美國的一些華人學者,誰是活寶誰是頑童,呼之欲出。《九七》一書我寫過三千多字的書評,書中的選美場面、舞廳景象,香港風味十足。作者言志言情言政治,馳騁幻想,莊諧並茂,為「九七文學」的別開生面之作。
Joe評論文學,和夏志清一樣,不以時新的批評術語作號召;寫小說,不走現代主義那條「銳意創新」路線。老派作家在某些新派學者心中,自然是落伍了。作為「學者作家」,Joe作家的一面,小說之外,還以散文(雜文)見稱。懷念之際,我又翻讀其文。我主編的《吐露港春秋:中大學者散文選》收錄他的《父母之言,搖滾之音——讀<美國人閉塞的心靈>雜記》一文,它代表了Joe書寫頗頻的一個類別。和夏公一樣,Joe喜讀《紐約時報》的書評附刊,看到喜歡的書,買而讀之,讀後寫成文章在港、台的報紙發表。他介紹新書,夾敘夾議,中文讀者得到新知,還欣賞到他益智有趣的文章。劉勰如讀到他令人「悅懌」的評介文章,一定喝彩。羅馬人賀拉斯如生於今日,一定給他個文學大獎。我就是劉文多年的受益人。
Joe是美國印第安娜大學的比較文學博士,其博論當然用英文寫成。在美國為謀稻粱,還發表了不少英文論文。寫中文,他用龍飛鳳舞的鋼筆或圓珠筆,把趣事卓見瀟瀟灑灑流露出來;寫英文文章呢,他告訴我,那是一字一句慢慢像「dao木」(粵語詞彙,拼整木料以成用具之意)般dao出來的。說到在威大上本科生的英譯中國小說課,要講張君瑞如何始亂終棄,吳保安如何棄家贖友,一想到明天要對洋青年講這些中國古代故事,晚上就先像「剝牙」(即拔掉蛀牙)一樣痛起來。Joe是性情中人,常顯率真漢子的作風。
回歸故園 絢爛無邊
1981年秋學季的相處之後,翌年曾同在紐約開會。大概是1983年吧,我向市政局圖書館的吳懷德先生推薦Joe來港在「文學周」演講,我們又見面了。他和德國學者馬漢茂組織舉辦「大同世界:中國現代文學國際研討會」,1986年夏天在西德舉行,夏公等都出席,我躬逢盛會,與Joe又歡聚一番。要特別指出的是,全球各地中文學者與作家「群眾大會」,此會開了風氣,有發揚大漢文學之意。
不同時期,在台北、在陌地生、在香港的中大、在嶺大,先後都有或長或短的聚會。
新世紀開始那幾年,會晤機會甚少,連那次Joe邀夏公到嶺大開會,我也失諸交臂。Joe可能認為我某些事行差踏錯,不與同行。
有多年甚少見面。2018年白先勇到嶺大講《紅樓夢》,Joe邀我跟內子出席,既聽講又聚餐,風雅且熱鬧,但Joe不再如前那樣指點江山、氣盛言豪了。臨別我對Joe和司徒秀英教授說:我們近年住在深圳,你們少到內地;何時移玉,我們一定盡地主之誼,兼任導遊,參觀這個現代化的香港鄰城。
中大出版社出版的數卷夏濟安夏志清書信集,以及Joe自己的文集《絢爛無邊》,我相信至少有幾本是Joe請中大寄來給我的。我也把新作寄給他。有好幾年Joe沒有回我書信,寇疫(Covid-19)肆虐,音訊更少。
近幾年中大出版社為夏公的《中國現代小說史》推出新版,又出版《夏濟安譯美國經典散文》,這些書都灌注了Joe的大量心血。我閱讀諸書,十分感動,寫了《老弟子傳芬芳》,2017年在《北京晚報》發表。
從1968年首晤,到2018年最後一次相聚,相隔正好五十年。讀其書,交往其人,可記可述之事甚多。Joe的論著、散文和小說,還有翻譯如中譯名著《一九八四》,還有為天地圖書公司編的「當代散文典藏」系列,各方面表現卓越,為學界文壇所推崇。其多種文類的書寫,也可謂「絢爛無邊」了。這個「香港仔」九十年代回來香港教書,回到他的家園,晚霞絢麗,終於落葉歸根。
我深深感動於Joe為兩位夏老師傳芬芳。劉教授在美國、在香港的弟子,我相信也會傳劉老師的芬芳。Joe長我一輪生肖,是我半個前輩。我四十年來寫過多篇文章稱道他的著述,也可說是傳Joe 的芬芳,傳一個文學漢子的芬芳。






0 / 255